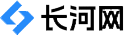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长河网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changhe99.com/a/oV6May256g.html
蔡锷(1882-1916)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撤销,师生皆离散。蔡锷、唐才质、范源濂等十多人打算到湖北武昌两湖书院继续学习,但以时务学堂旧生而被拒绝。蔡锷等人只得前往上海,于1899年6月投考南洋公学,并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在等待
原标题: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四:思想转变蔡锷(1882-1916)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撤销,师生皆离散。蔡锷、唐才质、范源濂等十多人打算到湖北武昌两湖书院继续学习,但以时务学堂旧生而被拒绝。蔡锷等人只得前往上海,于1899年6月投考南洋公学,并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在等待入学之时,他们接到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来函相召,并得到唐才常等人的资助,遂于8月东渡日本。到日本后,蔡锷即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该校由横滨华侨和日本有关人士共同筹资于1899年9月创立,梁启超任校长,日本著名教育家柏原文太郎为干事,授课教师除梁启超和徐勤外,另有日本教师6名,帮助学生学习日文及普通科学。梁启超后来回忆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时说:“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生除陆续来日的蔡锷、唐才质、范源濂等10多个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之外,还有从横滨大同学校转来的冯自由、郑贯一等人,加上以后陆续入学的共计30余人。上海南洋公学在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梁启超仍像当年在时务学堂那样,指导学生读书、讨论,批答学生的学习札记。不过,这次他要求学生所读之书不再是《春秋公羊传》、《孟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老师与学生所讨论的话题也不再是“孔子改制说”“三世说”“开民智”“兴民权”,而代之为“冒险”“进化”“自由”“权利”“平等”。因为梁启超经历惊心动魄的戊戌变法失败和在日本阅读了诸多近代欧美有关民主自由平等学说的著作之后,早已“思想为之一变”。进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蔡锷耳目一新,在梁启超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研习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的理论,师生所谈论的全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在一篇学习札记中,蔡锷探讨了冒险与进化的关系:“古今之大患,莫甚于以己之才力心思,不敢卓立绝出,而驾乎人之上,相率因循,以仰人之鼻息,承人之目耳,自窒其脑筋,束其手足,此贱丈夫之所为,甘于为人之奴隶者也。以为千万人之所是,吾独从而非之,千万人之所非,吾独从而是之,千万人之所闭,吾独从而开之,宁不为人窃笑乎?此终古所以无进化之理也。虽然,盖未知是非无定之理耳。夫儒崇乐,墨非之。墨救人,杨守身。古之所非,今以为是。此数百年以为是,后数百年必有以为非者。且以有形之草木禽兽,固无一定之象,况无色相无涯涘之公理乎!夫千万人之所非者是之,是者非之,闭者开之,梦之所不及者吾言之,冒险也。一人冒险,而遂开千古文明之境界,日本之藤寅是也。冒险者,进化之大原因也。原因甚微,结果剧大,可不勉哉。”梁启超批道:“英国大儒约翰弥勒曰:侵人自由之权,为第一大罪,自放弃其自由之权者罪亦如之。言自由之学者,必以思想自由为第一义,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则天下无复思想矣。”1899年梁启超(前右四)等人在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合影人的权利问题也是蔡锷研究的兴趣所在,他在札记中写道:“分民之阶级,与破除阶级之见者,优劣判若天渊,然无阶级中复有无穷阶级存焉。下等社会之人,不能有上等社会之权,即授之以权,则亦不能保守,其权即为无权,此天演之阶级也,人为每为天演力所抵制者此也。欲胜天演之力,非平世界之智慧不可,平之之道,其大发其原动力乎。进化之关键,舍此无由,则天演之力,转而为铸文明之具也。天演与人力所以互相胜负也欤。”梁启超批道:“自由权者,自得之者也,非人所能授我也。若人能以授我,则必非我之自由权也。授之以权,亦不能保守,此最可痛之事,然亦必然之理。然则寻常人骂独夫民贼之夺我民权者,是冤词也,己苟不放弃其自由权,谁得而夺之?凡被人夺者,必其不能自保守也,于人乎何尤?”接着,蔡锷又与梁启超探讨了自由与权利的关系问题。蔡锷写道:“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志于自由,必不可以夺之,可以夺之者必其不自由也。夫志尚可以夺之,则无不可以夺之矣。中国无具此不可夺之志,乌能与自由者享自由之权利哉!权利者,天下之公物也,己不能享之,人必代而享之,于人无尤也。无自由之希望,必不能有自由之力量,无其力量,则不能置足于大地争竞之场也必矣。夫希望之所至,力量随之,力量之所至,成事之现象随之,其效至速也。善夫中村正直之言曰:国家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有自主之志行,盖深知国家自强之大根原也。”梁启超批道:“志之自由,则思想之自由也,为一切自由之起点。权利者,天下之公物也云云数语,德国学者所称道之说也。”在另一篇札记中,蔡锷进一步谈及了对于国权与民权关系的看法:“国家之有主权,即代表人民之公共权也。权散于私民,则涣散而微小,归于统一,则强大而坚固,故不能不立一主权之国家。国家所主之权,国民所与之者也。国民之权大,则国家之主权亦必大,国民之权小,则国家之主权亦必小。此二权者有聚分之别,无上下之分,故所聚之权,常视其所分之权为大小强弱。故善治国者,常行其强大国民之权而舒伸之之政,故国家之主权,亦因之以强大舒伸,今之环球诸强国是也。不善治国者,常行其弱小国民之权而屈抑之之政,故国家之主权,亦因之而弱小屈抑,今之中国及土耳其是也。推及其初,不过逞一己之私,而侵夺人民之权,人民之权既就于消亡,而己之权随之以化为乌有,其眼光如豆,祗顾一己,不顾大局,祗顾一时,不及未来,野蛮人之思想作为种种如是,亦可笑已。”梁启超批道:“约翰弥勒言:专制之国,必无爱国之人,若有之则其君主一人耳,可为此文注脚。”对于西方一些政治家宣扬的美妙的世界大同,蔡锷难免心向往之:“演言谓:尚武人群,以农工商供兵役。农工商人群,以兵资保卫。上所言者,野蛮之世也,下所言者,近日欧美进化之世也。予以为进于化之极,必人人能伸自由之权,识自由之理,人人自为保卫,且无所侵争,则无所谓保卫,又何以兵力为哉。人心中有国界,故致有以兵平不平之事。他日合地球为一大群,欧亚美为腰腹,群岛为手足,天下豪俊为头目,公理为以太,又安有手与足之争,手足与腰腹之争哉,则无兵之世,可决而定也。”梁启超批道:“自由之理大明,人人不相争,自然无所用兵,且不惟兵无所用而已,即政府之职,亦不过以调停裁判其人民之偶有侵人自由者而劝止之,如斯而已。他事非所干涉也,政府犹然,而况于兵。”出于对“无兵之世”的向往,蔡锷对俄国首倡之和平会议也有几分期许:“俄倡设弭兵会,人多以诡诈目之,谓不足信,盖亦未之思耳。王阳明曰:未能知说甚行,故知先于行,空谈先于实事,一定之理也,迂儒何足以知之?夫天下事,每以空谈起点,而遂成其后,安知此时之欺诈,后日不得不转为至诚者?此时之出诸口,安知后日之不能见诸实事者?儒生议论,尚足以移动全球之大局,况昭昭然联为会者乎?即其不诚亦文明之先声也。而张之洞乃作非弭兵议以非之,抑何忍心倍理,甘为野蛮据乱之人耶。”这说明,此时蔡锷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还缺乏认识。对于这个敏感的现实问题,满腹经纶的梁启超也感到一时难以解释清楚,只好委婉批道:“虽然此理固是也,然合为一大群之后,则第二之原动力,无从发生,恐又变成退化之局,如中国此前千年之世界,然斯亦不可不虑也。汝试深思之,答此难。”但不久,蔡锷对帝国主义列强本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俄人之言平和,犹盗贼之言道德”。“以带甲百万之俄罗斯,而首倡万国平和之会,在常人之眼视之,以为恶兽结放生社,不过借此以弭天下之猜忌,而己乃得肆其爪牙而已”。“此弭兵之会,所以徒虚设耳”。由上可见,在梁启超教导下,蔡锷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由是高谈革命,多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联系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蔡锷慷慨激昂地表示:“大丈夫当视国如家,努力进行,异日列吾国于第一等强国之列,方不负此七尺躯也”。为达此目的,1899年秋,蔡锷与林锡圭等人发起成立东京九段体育会,以强身健体。不久,东京饭田町九段体育会开幕,蔡锷和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生都积极报名参加,每两天练习兵式体操及射击两小时。为了“联络情感、策励志节”,1900年春,蔡锷与秦力山、沈云翔、戢元丞等在东京成立中国留学生组织“励志会”,并创办《译书汇编》《国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鼓吹反清革命。所有这些充分表明,蔡锷此时的思想已经逐步由维新变法向民主革命转变。(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二章“留学日本”)责任编辑:
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