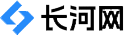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长河网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changhe99.com/a/yBrggggKrP.html
“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特别有趣的照片。一个美国年轻人在尼泊尔,披着长发,穿着东方服饰,被十几个当地男孩包围,这十几个男孩头部紧挨在一起,穿着欧洲服装,正在取笑他。即使他非常希望,他也不能向他们解释,他们所渴望的摩托车和汽车是一个幻觉,一种
原标题:米沃什:完全的人类平等将会实现,但这可能是被统治者的平等“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特别有趣的照片。一个美国年轻人在尼泊尔,披着长发,穿着东方服饰,被十几个当地男孩包围,这十几个男孩头部紧挨在一起,穿着欧洲服装,正在取笑他。即使他非常希望,他也不能向他们解释,他们所渴望的摩托车和汽车是一个幻觉,一种虚幻的面纱。”死者之舞与人的不平等[波兰]米沃什胡桑译死者之舞是中世纪晚期画家们的流行主题,有时,也出现在在巴洛克时期。在那种舞蹈中,所有社会阶层和职业的及从童年到老年的所有生活阶段的典型人物都跟随着死神,舞蹈的引领者。在终极存在中,农奴和乞丐与教皇和主教、国王和王子之间都是平等的。然而,除了贫民中革命的、宗教的异端邪说的追随者之外,没有人质疑人在尘世的朝圣之旅中的不平等,由他们出生的农民、自由民、贵族出身造成的不平等。后来,当人们被普遍承认为平等的时候,对这个口号在理论层面的接受并不同于其表达的完满涵义。虽然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一些人的货币特权,另一些人的错误做法,却造成了许多分裂,而其引发的耻辱只能强化这些分裂。我自己的例子就验证了这一点,因为毫无疑问,我是特权的孩子,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而言。我的父母重视教育,所以送我上学,但比起这些,我拥有更多的特权,因为在学校我享有很多特权,我的许多同学却没有。我熟悉大量来自工人或农民家庭的孩子们所不知道的表达和想法,并且我的学习并不努力,却学会了在言语和写作中正确地表达自己。从家庭中带来的这些资源至关重要,正如我后来观察到的,当我自己的儿子在法国上学,法国是最保守的国家之一,孩子们在十一岁时被分类——有些人会上“国立高中”,并立即被标记为上层,而其他人将为“较低层”的实业职位做准备。操练着读到的第一行文字“我们的高卢先祖”(NosancêtreslesGaulois),我的儿子们[1],显然没有一滴高卢人的血液,不能一个词也不能读懂。然而,在语言的使用能力方面,他们很快就超越了小学同学,大部分是工人和小商人的儿子,他们的要求就读“公立高中”的申请立即获得了老师认可。除了他们的先天能力,家里的书籍和三门语言,波兰语、英语和法语,我们用它们与朋友交谈,在这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读完了高中和大学,尽管,这没有使我免受奴役。有一段时间,特权阶层无需关心日常的口粮,但教育所确保的护卫已是强弩之末。文凭让人们从农场或工厂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却不能将人们从办公桌、绘图台或实验室的八小时工作中解放出来。所以,令我厌恶的是,我意识到,生活被分裂为出卖的时间和空闲的时间:前者不真实,枯燥乏味,不堪重负;后者真实,妙趣横生,丰富多彩——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错觉,因为疲惫让你无法利用空闲的时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更基本的分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出卖自己的时间的必然性是他们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的失败,就像接受死亡,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考虑到这一点,我自己的传记采取了特殊形式。我很幸运,我自己的冥顽不化起到了作用,此外,多种多样的历史环境不断地让我变得无权无势。我的奴役和富足的时期都很短暂,而我的彻底自由和贫穷的时期十分漫长。我通过写作赚钱,但大多作品是我喜欢写下的,写于我想写的时刻。甚至贫穷也不太令人恼火,或者也并不持久,因为我写的书给我带来了一些钱。今天,我对我的命运完全没有感到遗憾,即使长时间苦思冥想,我也无法想象一种比我所获得的更好的境况。多年来,我一直是自己时间的主人,我的生活并没有被分裂为两块。我不是说,我衣食无忧而不工作。然而,大学教授的职责,虽然对许多人来说是负担,对我来说不是;相反,我与学生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流逝在交谈中,与同事的沟通毕竟有着和在写作中相同的目标。我意识到自己的特权,因为“存在决定意识”(其条件是,一个人在这里不会将事情过度简化)这句箴言中有着诸多智慧;我承认自己的想法,即我的位置——一个比较高的,如果不是指财富,也不是指自由——有能力缓解我的愤怒、嘲弄和讥讽,对于这些,我们的人世已经提供了很多、甚至太多的理由。拥有特权的人总是知道如何安排事情,以便在讨论重要观念时,他们不用承认最简单的事情——他们的时日并不花费在所谓的艺术和科学的培养上。1981年,米沃什在波兰华沙大学为学生讲话。热烈地宣扬人类平等的诗人和哲学家真的相信,为他们端送咖啡的女仆、面包师、公共汽车司机和环卫工人是平等的吗?诗歌和哲学变得越复杂,他们越纠缠在由语言本身创造的丛林中,使他们不再能够接近,不仅是文盲或半文盲,甚至是那些有过正当教育的人,倘若他们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无辜的人,精神上贫乏的人,被指定去耕作土地,开车和乘公共汽车,烘烤面包,作为推销员而工作,他们的平等仅获得公平的薪水和安全的权利来表示,他们的安全来自于强者和国家的法律缺失状态。同样,受过教育的人,如果他们选择了良好的生活,而不追求更高的、精神的愿望,却被赋予应得的地位。旧的贵族秩序被一种新的划分所替代——牧师的等级,商人和战士的等级,主管者的等级。对于人类平等之真相的真实而深刻的经验是一件罕见和艰难的事情。也许它开始于认识到,诗歌和哲学,即使采用深奥的方法,并不是以纯粹智力为名进行的纯粹智力运作,而是与每个人都参与的死亡之舞有关,因此,它们,至少在潜能上,是为了每个人进行的。只有这样,卡尔·马克思所取得的突破才能受到赞赏。对于马克思而言,存在着一种唯一的人类本质,它被历史的紧急状态划分为了临时的,短暂的却持久的,这种本质勾勒了企业家、工人、知识分子、农民的形象。今天社会主义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世界各地,只有借用其发轫形态,我们才能找到一种新的、更充分发展的平等观念。波兰社会主义者扬·瓦克瓦夫·马察耶斯基[2]多年来一直被囚犯在沙皇俄国的西伯利亚,是第一个对未来的、后革命社会中的平等命运表示疑虑的人。他的论文,用俄语写成,以《思想工人》(MentalWorker)为名结集成书,于1905年在日内瓦以假名A.沃尔斯基(A.Wolski)出版。在评价整个压迫和剥削的历史时,比起职业革命家同志们,马察耶斯基的刻薄一点也不少,他不同于他们,他否认那一段历史,一个残酷和严厉的情妇,可以自行改变自己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反对“不可动摇的发展规律”,人们认为这个规律导向一个完美的社会。他怀疑革命运动会成为渴望权力的新等级所诉诸的诡计,即便这个等级那么富有诚意。这种思想工人的新等级不满于对资本家的依赖。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利用群众没收资本,然后掌握经济管理的控制权,使工人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劳动,而整个社会是与统治阶级一致的。马察耶斯基因此建议工人不要信任白领知识分子领袖,并从下而上创造自发组织——一种更激进的革命,在此种革命中,工人让自己掌握了经济。马察耶斯基的预测,普遍而言,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统治下的社会的反民主、等级结构迄今尚未得到分析,从而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生?”——即,有多少东西需要归因于对于教条的充满误解的或充满无意识欺骗的设想,有多少东西要归因于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移到国家手中时起作用的命运力量?工人的利益与那些直接垄断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行政人员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因此,就像东欧国家的许多反叛分子所渴望的,有必要从官僚手中夺取权力,并转交给工人委员会。这意味着普通公民的政治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超过我们所知道的雅典民主。这里的障碍是相当大的,但障碍似乎并不是起源于工人缺乏能力,他们虽然已是机智而清醒的思想家,却无法作出艰难的决定。毫无疑问,障碍被建立在生产和治理的机制中,对治理权的掌控需要持续保持警惕,几乎每天参加会议。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时代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集体行政仅只在少数情况下有效,因为人们的精力和兴趣只能够维持数周的革命狂欢,在此之后,专业人士,官僚分子,就接管了做出决议的繁重职责。如何控制他们,可以让他们维护工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那些处于管理机构顶端的人的利益,这仍然是一个谜。扬·瓦克瓦夫·马察耶斯基然而,“历史的加速”是一个事实;一场巨大的满溢刚刚开始,这是一场人类物质的洪水,如今此种物质被认为是一种单一的物质,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件,它不会迅速地在新的渠道中排解。这些规模的变化必须缓慢发生;如果以一个人的生命的长度来衡量,我就不可能有希望看到在某种程度上被安排得井然有序的世界。它必须满足我,让我见证人类所渴望的前所未有的觉醒。这些愿望形成一个整体,激发向上的运动。在工业化国家,在最低水平上,存在着一种动力从农村逃到城市,然后从体力劳动逃到任何其他类型的劳动,只要它不需要肌肉的力量。由于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以成功告终,普及教育可以造成巨大的痛苦和仇恨(“我懂得的和他一样多,可所以为什么他而不是我?”)但是,即使在更高的水平上,也绝不缺乏痛苦和仇恨,由于出卖一个人的时间不再被认为是人的必要条件,因此产生了对于“创造性”职业的不断增长的渴望,这些职业将工作和嬉戏,与不可逃避的“为什么他而不是我?”这个疑问联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大多数人,那些生活在欠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的人(事实是,贫穷国家越来越贫穷,富裕的国家越来越富裕)也有着其他烦恼。在那里,死于饥饿是一个日常现实,养家糊口,无论是什么工作,只要它允许一个人避免饿死,是一个不常实现的梦想。因此,在地球居民中我们微不足道的那部分人的渴望之中有着一些粗鄙的东西。这不是我的错,我如今关于人类平等所想到的一切都采取了非常美国的形式。弥足珍贵的贵族模式仍然静静地保留在欧洲。我足够清醒地将更多的美德授予美国的高中而不是法国的“国立高中”,虽然前者多数很糟糕,后者多数很出色。美国高中的入学向每一个人开放,不仅仅面向被择定的少数人。机会是不平等的,因为,例如,一个来自贫民窟的黑人必须吸收异国的观念和习俗,对于印第安人而言,他们正试图让他挤入的文明即具有排斥性,又完全不可理解。然而,选择的过程不适于儿童时期,而适于青少年后期,因为这个原因,它不太严格,从最贫困家庭中涌现出来的人物获得了辉煌的生涯,这仍然是一种现实。近乎普遍的中等教育,无论其质量如何,都指明了未来的轮廓;即,它邀请一种反思,当工作日进一步缩短,最后,大量的人,无论自愿还是被迫,都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小学,大学,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公民时间消耗的主要地方,它们在“后工业社会”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有一个词,今天几乎从来没有人使用,因为它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声誉——无聊。任何无聊的人通常不会承认它,而是会急切地保证,他只是被疏远了,是一个遭到遗弃的人,孤独,沮丧等等。但无聊,也被称为“厌世”(taediumvitae)[3],有关虚幻的知识,即一切的无意义,“厌世”(Weltschmerz,maldusiecle)[4],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不应受到轻视。在本书的开头,我谈到了由于空间的不稳定性在我们的想象中所造成的困扰,并最终成为无聊的根源。由想象力塑造的无尽空间可以比作帐篷的布墙,它要么绷紧,要么松弛并在风中拍打。上帝,作为一个中心点,所有的空间都可以与之相关,让布墙绷紧。在更小的规模上,将我们的思想从今天转移到明天的梦想实现了类似的功能。然后,我们周围的松弛空间以欲望的形式被投射到未来,由此变得紧绷——例如,终有一天我会来到现在想要游览的城市,终有一天我会开上现在想要拥有的汽车,终有一天我会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如果,无论是上帝,还是尘世的物品,或是集体企业,都没有提供具有方向的张力,空间就是惰性的,失去方向的,很快就会变得苍白无色。由于这个原因,同样,爱是无聊和异化文学中唯一的救赎;围绕着一个人的所有空间形式代替了上帝的处所。所谓的知识饥渴,似乎只有卑微的美德,一旦它开始防止无聊。新的不平等开始大光天下,并不是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些人有能力非凡,其他人则呆滞无能,有些人天性勤奋,有些人好吃懒做,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学校中被传授阅读、书写、描画的能力,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另一种方式。这种新的不平等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生活中避免无聊。独自一人组织完全空闲的时间需要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的激情,用以指导目标的设定和强迫性的自我约束,以便日复一日地接近这些目标。米沃什提到的《疯狂》(Mad)杂志。也许,正在为人类创造一个新的时代的,不是原子武器和星际旅行,而是作为大众的征兆的迷幻药物,民主意味着反对无聊。已经开始使用迷幻药物的那代人(借用了墨西哥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发现)不应该对其心怀蔑视地大肆辱骂,他们比,例如,二十多岁大呼小叫、满身珠光宝气的美国年轻人要强得多,虽然他们哗众取宠的姿态的确诱惑我们借用那句俄罗斯谚语:“让他们养尊处优,就是让他们变得疯狂。”在这里,我们可能正在讨论第一个在技术产品中被抚养长大的人类群体,他们将技术产品接受为正常的、日常的、纯粹实用的东西,这个群体很少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多如牛毛。此外,作为曾经酷爱《疯狂》(Mad)杂志的读者,整一代人在中学生涯中阅读着这本杂志,我认为,每天获取一点点残酷,技术文明用以嘲笑自己的超现实主义幽默,并非可有可无之事。(在欧洲,这种幽默直到最近还仅仅是波希米亚艺术家的私人密码。)最后,我必须补充一点,这里讨论的一代人是电视一代,正在收获电视所带来的所有后果,这是至关重要的,即便人们忽视麦克卢汉[5]的太不可靠的、总体而言错误百出的观念。这也是波普艺术的一代,这是一种难以理喻的艺术,对电视广告没有双重的、矛盾的态度。我试图尽可能简单地解释,我想象的是迷幻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在我看来,这是在尝试为实际空间赋予价值,致使创造意念空间变得毫无必要。这听起来艰深玄奥,但我不想吓唬任何人。有关实际空间,我想说的是,在既定的时刻,它环绕着我,我凭着五种感官领会这个空间。有关意念空间,我想说的是,它栖居于我的想象之中,召唤我去求索。这可以是上帝(总是考虑到我们的心灵的特定本质,而我们的心灵在空间关系的网络中被捕获),或者是亚哈船长的白鲸,或者是一个集体的历史目标(柏拉图“理想国”,更公正的社会,民族解放,等等)。很有可能,只有当我们朝着目的地穿过实际空间时,它才具有全部的价值(然后物质绷紧)。然而,化学手段可以改变我们的五种感官所接收的东西,我们周围的空间变得丰盈、无限丰富、自给自足,仅仅栖居于其核心就等同于栖居于神性之中,进入了艺术家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痛感;即,影像变成了声音,声音变成了影像。音乐在空间中建立了整个大厦,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桌上的烟灰缸和玻璃杯之间,颜色真正地“鸣响了”。对于一个真正具有宗教的人(这假设了一种获得神秘经验的能力,不应该与属于任何特定宗教团体的人相混淆),这或多或少在最普通的意义上其实是现实,在任何时刻由神的存在支撑着、照亮着。“知觉的敞开大门”提供了代理性的神秘状态,纵然超验的上帝被与世界一致的内在的上帝所取代了。本质上,化学在这里起到了反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作用,从而赞同东方的传统。这种神奇的药物产生了一种晦暗不明的影响。它剥去了禁令、规则和美德的面具;由社会所调节的一切现在似乎成了支离破碎的东西,普通人、“尔虞我诈的竞争”的奴隶们用来试图掩盖令人不安的、静默无言的存在的核心。反叛者们利用了这种药物,尽管它本身没有目标导向,而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缺少目标。与此同时,迷幻的仪式突出了将来某种更加不祥的特点。只过了三十年,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1932)就已不再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书。矛盾的是,在其临终时,赫胥黎还在提倡寻找佩奥特仙人掌(peyote)在化学上的对等物,因为它们可以给老年人带来有益的药效,减轻对死亡的恐惧。略早于赫胥黎的小说,斯坦尼斯瓦·伊洛纳齐·维特凯维奇的《贪得无厌》(Insatiability,1930)中就描述了服用默提-冰(MurtiBing)[6]药丸后引发的状态,几乎与服用麦角二乙酰胺(LSD)[7]的效果是一样的。在《贪得无厌》中,默提-冰药丸让人们对社会关系和历史灾难漠不关心,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对欧洲的征服[8]。当然,令人怀疑的是,具有化学般神秘性的福音的传教士目前由中国人谨慎地资助,中国人应该渴望在美国削弱美德。然而,这里为每一派系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们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机会。完全的人类平等将会实现,但这可能是被统治者的平等。人们将保证拥有幸福,然而条件是他们不干涉政府的事务。完美的化学手段将可以让每个人每天生活在神圣的空间中。但可以增加掌握知识和执行逻辑操作的能力的其他药物,只有精心拣选的少数人,管理阶层的成员,才可以获得。目前,这种整洁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不公正,贫穷,饥饿和大多数人的不满意愿望的损害。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特别有趣的照片。一个美国年轻人在尼泊尔,披着长发,穿着东方服饰,被十几个当地男孩包围,这十几个男孩头部紧挨在一起,穿着欧洲服装,正在取笑他。即使他非常希望,他也不能向他们解释,他们所渴望的摩托车和汽车是一个幻觉,一种虚幻的面纱。注释:[1]米沃什1944年与杨妮娜·德乌斯卡(JaninaDłuska,1909-1986)结婚,育有二子,安东尼(1947-)和约翰·彼得(1951-)。[2]扬·瓦克瓦夫·马察耶斯基(JanWaclawMachajski,1866-1926),波兰思想家,用俄语写作,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3]原文为拉丁语。[4]分别为“厌世”的德语和法语形式。[5]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加拿大媒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1951)和《理解媒介》(1964)等。认为媒介就是人的身体、精神的延伸。[6]米沃什在其著作《被禁锢的心灵》中对这种药丸有过详尽的阐述。[7]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ysergicacidLysergids,简称LSD),已知药力最强的迷幻剂。[8]指在1236-1242年间,蒙古帝国远征欧洲并进行残酷的屠杀和破坏,一度占领了匈牙利。(选自米沃什散文集《旧金山海湾幻象》,已获译者授权,转载请联系译者本人。)米沃什米沃什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著名的诗人、作家和散文家,曾在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暴露状态”。他的诗深处于现代主义诗歌传统之中,又以强大的内在形式穿透了混乱的当代生活,具有无与伦比的时间的力量。主要作品有:《被禁锢的头脑》(1950年)、《伊斯河谷》(1955)、《个人的义务》(1972)、《务尔罗的土地》(1977)。本期编辑:张晓敏欢迎转发、分享,其他公号如需转载,请与“未来文学”订阅号后台联系。责任编辑:
赞
(0)